过桥米线的老家是哪
过桥米线是哪里的?
大家肯定觉得我失心疯了,过桥米线,当然是云南的啦!
不信?请看这个耳熟能详的传说——
故事的确很美好,但……其实,这个传说,疑点蛮多的。
首先是来自维基百科的质疑——传说中的秀才是在蒙自南湖的湖心亭读书,维基百科认为湖心亭是民国时期才建的,与时间不符合。
不过,搜蒙自当地官网,上面就记载着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蒙自县事就在湖心修建了六角亭,并取名瀛仙亭。虽然维基百科的说法也不靠谱,但康熙年间,还是和“明末清初”差了一点。
怀疑这个说法的不止是我,还有大吃家汪曾祺先生。他在《米线与饵块》一文中在谈到过桥米线这个传说时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过桥米线’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此恐是出于附会。”云南美食界扛把子敢于胡乱也对这个传说不不屑一顾,他的《云之味》一书中这样说:贤妻良母一个不小心在厨房妙手偶得,失误做出个过桥米线。相似的美丽失误,上下五千年,多次出现,而且涵盖各个领域……
是额,林林总总的“从前”“有一天”的“美丽失误”,真的是巧呢!
秀才是杜撰的。那么,过桥米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在云南当地有好几个版本,主要分为蒙自说和建水说(建水是与蒙自同属云南省红河州)两个系列
建水说听来靠谱很多,因为人家有名有姓,时间地点人物五个w都全了:清咸丰年间,临安(建水旧称)县城鸡市街有一家名为宝兴楼的米线馆,老板叫刘家庆。某日,一个举止文雅、穿着讲究的人到宝兴楼吃米线,不过这人不走寻常路,偏要按自己的方法吃米线:跟刘家庆叫了碗刚开锅的肉汤,另用一碗抓入米线,再来盘片好的生肉片,然后将生肉片和米线先后挑进滚烫的肉汤中一涮,便开吃了。后来这人天天来吃,天天如此,就引起刘家庆的注意,自己也照着吃了一次,发现味道果然不一般,连忙请教。原来这人叫李景椿,多年在外省做官,常常吃“涮锅子”,返乡后便到宝兴楼仿照用“涮锅子”方法吃米线。被问及这叫什么米线,李景椿用筷子指着门外的锁龙桥笑答:“我从桥东来到桥西吃米线,人过桥,米线也过桥,我这吃的是过桥的米线。”
“过桥”的名字真的就跟一座桥有关?当然,在云南当地还有一种形神兼备的说法是指从米线碗中将米线挑入汤碗似过桥……纠结如我,如此这般牵强附会的说法真的让我很难相信……而且,既然仿照的是“涮锅子”,为什么不叫涮米线?
翻越云贵高原,让我们暂时离开过桥米线的公认发源地,来到——
苏州。
是的,在苏州人最喜欢的苏式面条里,我们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字:“过桥”。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中,主人公朱自冶最爱去苏州一家叫朱鸿兴的面馆,他往店堂里一坐,跑堂就会喊:“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浇要过桥,硬点!”在这一大串苏州面馆“黑话”里,陆文夫解释了“过桥”:“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搛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嘴里……”
在《品味口感苏州——小吃记》一书中,还有一个说法是苏州方言中“浇头”与“桥头”互为谐音,所以所谓“过桥”,实为“过浇”。这种说法在丰子恺《吃酒》一文中得到印证:“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作‘过桥面’。”
身为北方人,无法直接辨识这个方言说的真假。然后,我查了这款“汉语方言发音字典”,然后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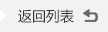





 扫一扫,进入手机站
扫一扫,进入手机站 关注官微,动态时时有
关注官微,动态时时有